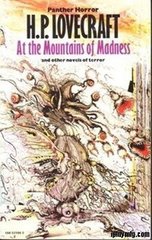朱文(中国内地男作家、导演)

朱文
中国内地男作家、导演
朱文(1967年12月-),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毕业于东南大学,中国内地作家、导演。其创作的个人首部小说是《到大厂到底有多远》,由他执导的首部电影《海鲜》,曾获得国际电影节“当代电影”竞赛单元评审团特别奖。由其执导的《云的南方》曾获得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其代表作有《因为孤独》等。
| 中文名 | 朱文 | ||||||||||
| 国籍 | 中国
| 出生地 | 福建泉州 | |||||||
| 出生日期 | 1967年12月日
| 毕业院校 | 东南大学动力系 |
| 职业 | 作家、导演 |
| 代表作品 | 《到大厂到底有多远》《巫山云雨》《我爱美元》《海鲜》《云的南方》 |
| 主要成就 | 第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导演 |
人物生平
朱文,男,1967年12月生于福建省泉州市。198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动力系,获工学学士学位,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写作,1991年开始小说写作。1994年辞去公职,现为自由作家。
着有诗集《我们不得不从河堤上走回去》,小说集《我爱美元》《因为孤独》《弟弟的演奏》,长篇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等。为20世纪90年代青年作家代表人物之一。
1998年,他发起主持了一次名为“断裂”的活动,向全国73位青年作家发出问卷调查,促进文学界对现存文学秩序进行反思。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触电”,写过的电影剧本有《巫山云雨》《过年回家》《火车,火车》《海南,海南》等。由朱文自编自导的电影《海鲜》,在9月刚刚结束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评审团大奖”。
朱文永远是个异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不在江湖中”。
如今他的小说已经和方文山的歌词、崔健的摇滚乐一起收录到了大学课本之中,朱文怪不好意思的,“那时还年轻,写起来肆无忌惮,那些东西还是不适合给孩子们读。”人到中年,朱文突然变得安分起来。曾经的他,还和作家韩东、画家毛焰一帮南京文艺圈的哥们混过,“那绝不是为了交流创作,就是为了吃喝玩乐。”而现在的朱文,戒了六年烟,结了三年婚,不开车,不喝酒,平时爱遛狗、爬山、喝普洱,他决定让自己“活得明白”。
在《小东西》的结尾,主演毛焰和托马斯在一起喝的就是普洱茶。毛焰告诉托马斯,这普洱茶不是二十年的,也不是十五年的,而是十年陈的,老外托马斯回答道:“十年,but good enough!”这便是朱文对友谊的注脚。“我喜欢一切带有时间痕迹的东西。俗话说,三生修得同船渡。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碰到一起,讲究的是因缘。”
几乎所有采访者都会问朱文一个同样的问题: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艺术家,你的创作到底来源于何处?朱文每每都会给他们两个字:“天赋”,紧接着再加上一句“虽然我讨厌使用这个词。”
的确,1994年之前,他还是南京一家国企的锅炉工程师,他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既不是小说,也不是诗,而是一篇关于锅炉结构设计的专业论文。由于父母在“文革”期间受到了巨大的打压,“思想活络”的朱文从小就让他们担惊受怕。学理科,是父母的要求,安分守己地靠手艺吃饭,那是他们对他的期许,却没想到朱文还是走上了艺术这条道路。
要是在不开机的时候,朱文的作息是很正常的。“甚至有点老龄化”。他一般六七点钟就起床,拉起他家那只才五个月大的金毛狗,下楼去散步,“我是我家小区花园的最大受益者”。于是,一路上,小说家朱文会遇到各种闲散的保姆和老人,他边遛狗边端详着他们,故事早已在脑海里萦绕不去。“通常,我的脑子里就有十个故事,那你就让它们漂浮在那里,并不理会它们。就等着看哪一个故事迫使你把它写出来。”
现在,总有人会要求朱文提炼一下自己这仅有的三部作品,来谈谈它们共同的主题。每当这个时候,朱文总是会回到自己的原点。“以前以为自己拍《海鲜》,那纯粹是种偶然,后来想想,却是必然。
我老家靠海,爷爷爸爸都曾当过渔夫,靠海吃饭。我成长在内陆,从小别人家都吃淡水鱼,我家却总是吃冰冻海鲜。我一直很奇怪这到底是为什么,原来,一切都流淌在你的血液里。《海鲜》带我回到海边,《云的南方》带我来到山那边。我所有的艺术,一贯的意愿都是想摆脱万有引力。
经历
1998年,他发起主持了一次名为“断裂”的活动,向全国73位青年作家发出问卷调查,促进文学界对现存文学秩序进行反思。
1990年代中期开始“触电”,写过的电影剧本有《巫山云雨》《过年回家》《火车,火车》《海南,海南》等。由朱文自编自导的电影《海鲜》,在2001年9月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评审团大奖”。
关于朱文的电影,其实我们知之甚少。比如《海鲜》,比如《云的南方》—《海鲜》连盗版碟都没有,《云的南方》曾在中央台的某个频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播放过,而且据说是在深夜。
朱文本身也很少谈自己的电影。他在这方面,有惜字如金的意思。他很少出现在媒体,但他也不神秘。至少,他没有把自己打扮得很神秘。他可能要比过去胖一点,衣着普通,一脸和蔼笑容。他不倨傲。他出现在清华南门的某个咖啡屋里,戴着一顶帽子四处张望。这时候,他有点像他过去的青春期,张望着,逡巡着。
这就是朱文,非常具体,身形高大,但是无法继续了解他的前史和未来。任何一个热爱过文学的青春期的文学青年都有可能热爱过朱文十年前的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我爱美元》以及《人民到底需要不需要桑拿》,他的小说那么特立独行,极度个人化,荒谬而滑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那是所有人的青春期吗?
朱文的敏锐在于,他比任何一个人更快速地记载,并且,迅速放弃了写作的营生,投向他更热爱的电影。就像1994年,一个持有两千吨级司炉证、擅长在图纸上雄图伟略的杰出工程师,突然打算离开这个游刃有余的岗位(也有传说是被开除的),开始不靠谱的写作生涯。他
知道自己天生是一个作家。他现在又要证明他天生是一个导演,他不认为陈凯歌、张艺谋是天才导演,因为他们都没有原创性,只依赖于摄像和剧本。他的自信是经过验证的,所以并不令人生厌。
曾经的叛逆青年
朱文早先参与编剧的电影《巫山云雨》、《过年回家》早已被很多人所熟知。而《小东西》是朱文继《海鲜》《云的南方》之后执导的第三部电影,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电影都没得到大范围的公映。外界对朱文新作品《小东西》的评价是:虚构,现实,武打,外星人等种种元素。在朱文眼里,“这部电影在我三部电影中是最简单轻松的,但是花了最长的时间,前后用了三年。”
无论是当年向传统文学发起的“断裂”行为,还是朱文诗歌、小说里所透露出来的气质,朱文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在不断书写他自己,他的反抗、愤怒。
朱文说,他不厌其烦地写那些小人物,只是在重申一种自由,这种自由,在他年轻的时候,它体现为一种对抗,一种愤怒;但现在,朱文变平和了,虽然朱文疏远依然。“他只是变得善于在愤怒与制度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作家韩东印象里,“从未见过朱文暴跳如雷,和人恶语相向。
即使是在和心怀叵测的评论家们面对面的交锋中,他也始终面带微笑,挖苦中不失调侃,和对方的恼羞成怒形成了极强的反差。”
朱文表示,像“傻×”这样的词并不像很多人理解的那样粗鄙,而是中性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和当时一种情绪的表达。所以,他说,爱情,你真像一泡屎,用叛逆和颠复来掩饰他对更美好事物的向往。因为大家都知道,朱文有一个漂亮女友,叫金子。
离开南京
1989年,朱文从东南大学力学系毕业,分配到国家重点工程华能南京电厂筹备处,而后成为机组控制室的司炉,操作控制一个巨大的锅炉,并且是三班倒,他就利用中间休息的时间写作。经过五年时间的创作,1994年,朱文辞去公职。再后来,他离开南京去了北京,有一段时间,因为父母和一些朋友都在南京,朱文要在两个城市跑。
朱文说,经过多年的争取,他自己的力量已变强大。
朱文并不是个很喜欢闹的人,即使因为拍电影,需要和人打交道,也没能改变他和别人之间那种很简单的关系。早先,他甚至会和韩东一起在大街上看来来往往的人群,并对其中的女性评点一番。但有一天,他还是舍弃了这份乐趣,离开南京去北京。
朱文发现,南京有很多朋友,他没办法安静下来。“北京太大了,要找什么人一起玩不是那么容易。”现在,更多的时间,朱文会呆在北京郊区的家里,也基本不跟什么人说话。朱文否认这是一种孤僻,他说,跟女朋友跟家人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难忘大厂生活
朱文有一篇小说《到大厂到底有多远》,描述了去南京郊区大厂时的一段坐车经历,冷峻而又温情,在其众多小说中并不是很起眼,但后来却被很多评论家一再提及。
很多人认为,朱文开辟了写小说的地理概念,自他以后,不少作家都喜欢在其作品中描绘身边的公交、街道等等,并作出对生活看似冷静的剥离。他的《段丽在古城南京》《达马的语气》都堪称是其中的经典。那些熟悉的南京地名和日常生活,虽然仅仅作为一种疏离的背景出现,但这正体现了朱文作为一个异乡人对南京的特殊情感。
“那时有大部分时间在全国到处乱跑,但在南京大厂工作的那五年对我整个的影响实在很重要,走到哪儿,别人还是会习惯说这是从南京出来的作家。只是,我不喜欢那种重复性很强的事情,我很喜欢电厂的工作,因为它有价值感,每天都在创造财富,但重复……5年对我来说已经是极限了。”
写有那么多关于南京的小说,已在国际影坛赢得不少声誉的朱文并没有忘记南京这个地方,他表示,在适当的时候,用电影来展现对南京的所思所想并不是不可能。
本质性作家
南京有一个著名的诗人作家圈,他们作为一个团体的名字叫做“他们”,这拨人是韩东、朱文、于小韦、丁当、吴晨骏、刘立杆、鲁羊以及年轻一辈的曹寇、赵志明等人。朱文当年在工厂当锅炉工,在三班倒之余拼命写作。
到1999年为止,朱文总共写了80万字,觉得自己写得够多的了,自那后再没写过一个字。直到现在,他的声名也远没有达到大众化的程度,小说的印量很小,一直不太容易买到,爱好者们以在论坛上传贴其小说并交流看法为乐趣,可以说朱文是作家中的作家,在写作圈内具有相当大的力场,他的写作影响了一批人,不少年轻作家如李红旗、李师江等都自承深受其影响。
朱文的写作深入了每一个人的存在状况,他以高度的耐心与热情去描述吃喝拉撒、无目的的游荡、突如其来的意外,展示生活中最百无聊赖、最微不足道、最容易被我们自己忽略的琐屑细节,陌生、荒诞,然而这又正是我们所熟悉而又麻木不仁的。他说,“无聊之处见真知”。
他的笔下有无聊而躁动不安的年轻人,有压抑了大半辈子的老年人,有破罐子破摔的艺术圈女性,他不替他们辩解,也不对他们作出评判,他尊重并理解这些人,让他们自主地在各种关系和命运里浮沉,在迎面而来的诱惑和打击前,或是一再被羞辱,或是偶然地重获尊严。
朱文曾说,“一个好的小说家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首先对他自己而言必须是必要的,它只能来自你诚实敏锐的心灵。写出一个你的能力可以达到的最高级、最完善复杂的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出应该写出的与你有着血肉联系的那个故事。我把后一类作家叫本质性作家。我很难接受还有另一类作家”。
现在他补充说,本质性写作的意思是要回到源头,回到最初的感动。他拒绝让那些貌似深刻、貌似博大的因素渗入到写作中,他说,“对一个严肃自律的作家来说,他最糟糕的作品里也有着隶属于他本人的当时的最紧张的心灵焦灼”,写作是一个自我沟通过程,与自己的心灵共同生活。他还说,“我精神上对写作的需要远远甚于写作对我的需要”。
这样的态度体现在他的小说里,他的小说有一种直面并深入现实与心灵的精神品质,独立并强悍,不讨好不避讳,不自我感动也不试图感动、怜悯他人,像一个挖土机一样看准地方直接挖掘下去,入木三分又势不可挡。他的语言酣畅淋漓,飞扬,恣意,兴之所至,读起来非常痛快。
彻底地抛弃既有的标准,向许多事物发起进攻,必定要遭到很多人的反击,1990年代中后期,《我爱美元》出来后,朱文被人称为“流氓作家”。
《我爱美元》并不算朱文最好的小说,但因为其激烈的反叛姿态而成为他最出名的作品,它写的是“我”带着父亲找小姐的事情,这部小说几乎让朱文的父亲身败名裂,朱文由此深感这种老是写“我”的方式很有祸害。
自我分析
在朱文十余年的小说生涯中,其作品有一个明显变化,就是早期的小说往往以“小丁”即“我”为主角,围绕“小丁”的心理情绪和游荡行为而展开,主观性很强,有很多“小丁”的直接独白。而在后来的小说中,“我”通常成了旁观者,目击他人的挣扎、放任或沉沦,“我”不再处于中心位置。这个转变很重要,一般认为他后来的小说更成熟,叙事更精湛,视野更广阔。
早期的小说有《去赵国的邯郸》《弟弟的演奏》《我爱美元》以及《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等作品,这些小说都打上了主人公“我”即小丁的强烈印迹,小丁—一个叛逆、怀疑、喜欢四处晃荡寻找刺激的年轻人,他的内心被虚无感包围,处于极度的焦灼之中,他质问、愤怒、寻求、忍受,跟自我左冲右突、不得安宁。《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中,小丁向父亲问了一个憋了很久的问题,“你已经活了那么大岁数了,为什么不想到去死”。我还记得几年前看到这个地方时所受的震惊。
“我”还会置身事外般成为另一个我的旁观者,身心分裂。《弟弟的演奏》中,“我”被迫与脸色腊黄、切除子宫的女上司栾玲保持令人恶心的性关系,“在激情丧失的尽头,我没想到厌恶也能成为另一种激情”,这时栾玲要求中止这段历时两年多的罪恶关系,“但是我不答应,我坚持着,我要看到自己欲望的界限”,“我知道我的热情没有方向,没有结果,没有意义”。也许这种热情便是加谬所说的“荒谬的激情”。
这样的自我关系是异常紧张的,这样的写作方式对于写作者而言意味着非同一般的残酷,在如此激烈的对撞中,写作者很难全身而退。所以韩东说:“朱文的方式就是要不断地回到自己,把自己当作了一条道路、一座桥梁,流淌于天上地下的‘精神之流’将从此经过,伤及自身。这样的写作是献身性的。但不因献身的意义而变得悲壮,同时他也是坚实而痛快的。”
朱文后来的小说更愿意讲故事,不再跟自我周旋,与早期的相比,写作变得明快、收放自如;语言也更加酣畅,有一泻千里之势。有两篇已经成为了写作圈内的经典,它们是《段丽在古城南京》和《胡老师,今天下午去打篮球吗》,都收入了朱文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达马的语气》中。段丽,一个混迹于艺术圈内的女人,被一个无耻的画家骗走了爱情和金钱,她试图怀上他的孩子,在躲往乡下的时候被追上,腹部被一阵猛踹,从此后段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滥货。
《胡老师,今天下午去打篮球吗》的故事是这样的,年轻时的胡老师在打篮球时认识了范红,最后碰见时范红的眼神有些异样,后来范红跳河自杀,她留下的私生子小强被胡老师夫妇收为养子,之后经历了爱人病故、儿媳出走、儿子离家,胡老师一个人带着孙女小兰过活,小兰越长越像范红。“
想到了范红,我就想到了篮球,就想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就想到了我久已淡漠的压抑。我多次做梦又梦见自己在球场上奔跑,梦见球场上那一次次短暂的身体接触。人是多么软弱呀,尤其是像我这种行将就木的人,我根本没有力量去对抗那只已经在铁笼子里被禁锢了几十年的野兽。
在小兰十三岁那年,我终于做出了那件令人不齿的事情,并以此否定了自己不足称道的一生。”他这才明白当年范红看他的最后一眼,那正是已埋伏好的命运。
可怜又可厌、破罐子破摔的段丽,和一生多难、被命运绊倒的胡老师,这些在生活中受尽伤害和羞辱的男女,在朱文的笔下,终于获得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他说,“他们不是什么特殊的人,他们就是我们”。
参考资料
1.朱文·名人简历